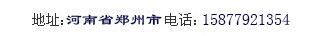(下篇)
(徐铎摄于瓜皮岛)
老枣树的枝桠上,已经让网梗磨出了一条凹痕,磨去了皮的老枣树裸露出紫红色的血痕。春夏秋三季,青青都在老枣树下织鱼网。到了冬天,那手冻得像猫咬得一样疼,她才不得己挪进屋里,将网梗吊在房梁上。屋子里空间狭窄,房梁也低,织网的人本来就在穿梭编织大网,在堂屋里,青青真找不到织网的感觉。
婆婆点亮了油灯,走到堂屋,她说,青青啊,睡觉吧,别织了,大海里的鱼鳖虾蟹到了冬天都要猫冬,你一年到头地忙,到了数九寒冬,你也该歇一歇了。听妈的话,睡觉吧,网梗一直绷着,早晚会断了。
青青这才爬到炕头上,婆婆往灶洞里填了一把玉米秸子。灶洞里闪烁着跳动的桔黄色的火焰,渐渐地,火势也奄奄一息,火光也黯然了,一缕惨淡的月光透过窗棂,照射进屋里。冬天的夜晚,没有野虫的,寂寥而宁静,没有一丝生气。偶尔能听到一两声狗叫,从叫声里也听得出来,那狗叫声也无敌意。狗有穷精神,夜里只是打盹,而不会睡觉。狗能发现窃贼,也是能看得见鬼魂的动物。这时辰叫,它一定看见了鬼魂。月黑夜盗墓的人为什么要牵条狗,为的就是让狗吓跑那些鬼魂。
枕头旁边,放着青青织网用的梭子,这把梭子是竹子做的。因为要织鱼网,是婆婆用过的梭子。原本黄黄的梭子,已经让青青的汗水给浸润得变了颜色。因为不停地织网,梭子已经磨得十分滑腻,只是青青的手让梭子打磨得皲裂粗糙。青青已经对梭子萌生了感情,她用手不停地抚摸着梭子,将梭子轻轻地贴在面颊上,本来尖尖的梭子尖也已经不再尖锐,扎在皮肉上面,也不会产生痛感。冬至过后,到了数九寒天,因为没有渔船靠岸,鱼挑子也很多天没有到海青岛来了。今年最后一盘网快要织好了,不知他什么时候来取,或许要等到明年开春吧……
大清走了以后,鱼挑子算是第一个走进她这寡妇小院的男人。公公婆婆说,人家是给她们送生活来的。没错,如果没有鱼挑子送来织网的活儿,他们一家人的日子不会过成这样,春节前,青青给公公婆婆都做了新衣服,甚至给他们预备下了送老的衣服。青青给公公选的是藏青色的绸缎,给婆婆选的是紫红色的锦缎,海头上的老人,生活宽裕的,都是活得里旺旺兴兴的时候,就预备好送老衣服。大清爹妈从未有过这样的奢望,丧夫的儿媳妇替他们做到了。
青青也给“彪”小叔子也做了新衣服。这个一直给锁着男人从未穿过新衣服,等到青青把新衣服送到他面前,让他脱下旧衣服,换上新衣服的时候,青青看见,彪小叔子眼眶里面有泪珠在打转。
青青觉得怡然,因为她感觉到了,即使是精神不正常的人,他也知好知坏,他也有感恩的意识。自从青青走进这个家门,那个一直给锁着的年轻男人再也没有犯病,一直很温顺,很安宁。“彪”小叔子像他哥哥一样英武,有男子汉的气度。青青总是听到人们议论她的丈夫大清,说他是海青岛上最了不起的船老大。
青青睁着双眼,她一直没有入睡,几乎天天如此,总是要熬过下半夜,她才能昏昏沉沉地似睡非睡地合一会儿眼睛。自从这把梭子成了青青的伴侣,青青找回了童年时,妈妈拍打她入睡的情景,妈妈会哼着自己编造的歌谣,好宝宝,睡觉啦……懵懂的记忆,逝去的似乎并不久远,她睡在妈妈的怀里,或睡在妈妈盘着的腿上……直到她长大懂事了,她也耍赖,非要睡在妈妈的身旁。她撒着娇,我就要妈搂着我睡觉。妈妈感叹着,等到你长大出门子了,就会有人搂着你睡觉了……
女人的幸福,就是小时候有妈妈的爱,长大以后,又能得到男人的爱。青青没有得到丈夫的爱,她觉得丈夫是个不幸的男人,在新婚之夜,他甚至没来得及爱抚她一回,就早早地离开了人世。人世间的温情,男女之情,他都没能获取。大清在青青的记忆中渐渐地淡化,他留给她的每一个细节,她都要努力搜索,才能找得到。这怨不得青青,她与大清接触的太短暂了。男人和女人的贴肤之亲,切骨之爱,她和他均没有感受得到。对于青青来说,不能不说,是人生的悲剧,也是做女人的悲哀。在生活当中,对性的渴望,除了来自于本身的那种萌动,还有周围女人们的闲谈末论。就连饲养的鸡鸭鹅狗们发情季的举动,她也感觉好奇与神秘。每天的劳心费神,虽然消耗了她的大部分精气神,她的这种神秘的渴望却没有淡化,每天剩余的那点属于她的睡眠时间,她也常常难以入睡。灶洞里的柴火渐渐地燃尽时,她身子下透过了一丝暖意。拘谨的身子舒坦开了,她轻轻地合上了眼睛……一个男人的身影出现在她的眼前,是大清?还是鱼挑子……他很健壮,肩膀很宽厚,肌肉很发达,能看得到那一丝丝的肌腱。他生着一双大脚板,五个脚趾像五根钉子一样,紧紧地钉在船板上。又像是野兽的爪子一样,牢牢地勾住了悬崖的岩石缝隙。这些时日,他经常出现在她的梦境,虽然他的影像模糊,但他们都是距离她最近的男人。他究竟是谁似乎并不那么重要了,他敢于走近她,他扳过她的身子,将她紧紧地搂在怀里。她已经感觉到了男人的气息,汗味里面夹杂着猛兽一样的雄性气息。那双粗糙的大手,抚摸着她的脸庞。几根粗大的手指拢着她面颊上的头发,并将她的头发拢到了她的脑后。他的手沿着她的脖颈,抚摸她的肩膀,她的肩膀浑圆而丰满,她紧紧地依偎在他的怀里,这让她想起了曾经避雨的大树下面。雨越下越大时,雨水顺着树干流下来,前来迎接她的父亲把衣披到了她的身上……那双大手开始触摸她的身体,她那敏感的胸脯……她记着妈的叮嘱,女孩子的乳房最金贵,结婚以后,只有自己的男人才可以触摸它。生了孩子以后,女人的奶子就属于孩子,女人的奶子能耗分泌出奶水喂养孩子。他的手触摸到了她的乳房,她感觉一阵晕眩,一阵颤抖,直接刺激到了她骨子的那根神经。她的身体微微地抖动着,那只大手并未停下来,而是继续向下,顺着她的腹部,继续向下。本来她紧紧地夹着的大腿可似乎已经由不得她控制,一直紧紧崩着的肌肉也松弛了,她愿意让那只大手滑进属于禁区的身体禁地……她的身体已经微微泛出了一层细细的汗珠……
(刘全华摄影)
青青从睡梦中醒来时,她的手里紧紧地握着那把织网的梭子。梭子上面沾着她的汗水,浸润着她的体液,她不由得羞涩地骂了自己的一句,不要脸……
青青很珍惜这把梭子,不用它的时候,她就把梭子放在枕头下面。这把梭子的颜色每天都有变化,只是青青瞧不出来,就像她容颜一样,每天都在老化。
开春时节,鱼挑子又敲开了青青家的院门,他是来取织锦好鱼网的。青青把织好的鱼网交给了鱼挑子,鱼挑子付给她钱,然后,又从筐子里面拿出一捆斩崭新的鱼线,交到了青青手里。
鱼挑子走了,青青一直望着他的背影。
站在身后的公公说,这个人心眼好,体格也健壮,是个靠得住的人。
青青没说话,转身走开了。
自从鱼挑子走近大清家的院子,自从青青给鱼挑子织鱼网,就有人议论,青青可能有相好的了。这个传言没有多久,便自消自灭,没有人再去议论。其实,最先说出这个谣传的,就是红英。她觉得,她也是个寡妇,可关于她的溢美言词却并不多。说起青青,人们总是赞美有加。大清哪辈子修来的福气,他死了,他娶进门来的媳妇却替他出力尽孝。乡亲们为什么不再相信关于青青的过耳传言,因为乡亲们亲眼所见,这些年,青青的所作所为。一个珍惜名誉如同生命的女人,怎么可能会做出那苟且之事。在此之前,也有过传言,说是青青不肯改嫁,大清不在了,青青跟她的公公不清不白地扒灰。再后来,又传言青青的“彪”小叔子所以没有再发疯犯病,因为青青与小叔子也有染。后来,这些挺恶毒的传言都不攻自破,不仅没有毁了青青的名声,反而让乡亲们更加看清了青青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。这些年,青青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,她用女性的贤惠,用女性的善良,征服了整个海青岛。有个海猫子不知潮流的女人背后嚼青青的舌头,海岛上的女人不但不相信,反倒将这个长舌头女人痛扁了一顿。
青青的公公去世之前,他把二大爷找来,他说,你是大队书记,你说话算话,等到我们老两口子死了以后,你把我那彪儿子送进精神病院,无论如何,也要让青青改嫁。这样拖累青青,我们做老人的就是伤天害理呀。
二大爷也答应了,他还保证,虽然新社会不讲这个,但他还是想留下话来,以后,要给青青一个说法,虽然不能立个贞节牌坊,但可以树一通树新风的碑。
二大爷在大队会上说起立碑这件事,队委们都没有意见,因为青岛的老人们经常拿着青青教育自己家的晚辈。咱们守海巴沿的人家,丈夫出海打鱼的,家里的女人更要守妇道。青青就是一个难得的榜样,让海青岛的大姑娘小媳妇好好地向青青学习。
红英对此有意见,她说,如今是新社会,再说,我们共产党也不兴这个,因为这是封建迷信,什么贞节牌坊烈女碑,就是封建统治者愚弄老百姓,把妇女当成牺牲品殉葬品的把戏而已。
二大爷是海青岛的一把手,他也是海岛上的当家人。本来他说话一口唾沫一颗钉,人人都听。可红英提出的反对意见,句句字字都在理,连二大爷也不好反对。不过,他与大队贫协的人说了他的想法,要给青青立块贞节碑。贫协的人说,立贞节碑,那是青青百年之后的事情。现在谈论,有点早了。
二大爷说,我就是想让你们记着我的话,我老了,一旦我死了,你们别忘记给青青立块贞节碑。
青青的公公去世以后,她的婆婆身体也一下子垮了。本来,婆婆还能帮着青青做些家务。这回她病倒在炕上,自己都顾不了自己。婆婆生了什么病,谁也不知道。村子里只有跳大神的巫婆和神汉,他们只说青青婆婆是邪鬼附体,只能驱鬼去邪。可折腾了半天,婆婆的病也不见好转。
那天,正好鱼挑子又取鱼网。等到他收了青青织好的鱼网,付了手工钱,又把一捆鱼线送到青青手里的时候,青青说,这一盘网,可能要费些功夫。
鱼挑子问,怎么了?
青青说,俺婆婆生病了,躺在炕上不能下地。
鱼挑子说,俺能帮上你什么?
青青说,能不能帮俺找个大夫,给俺婆婆看看病。
鱼挑子说,俺一定给你找来县城最好的大夫。
鱼挑子说到做到,他真的请来了县城最好的大夫。
婆婆听到这话,她说,青青不要请大夫,你爹走了没过三年,他是非要带上俺走不可。我跟着他去吧,省得他一个人在阴间闷得慌。
青青说,有病咱就治病,俺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遭罪。
鱼挑子把县城里最好请到了海青岛,他私下里不知给了大夫多少好处,那大夫才肯跟着他走了二十里山路。走到海青岛时,大夫已经累得快要不行了。歇了半天,大夫才给青青的婆婆看病。青青婆婆患的是肾病,挺重的,她的腿已经肿得老粗。俗话说,男怕穿靴,女怕戴帽,意思就是等到女性病人的头部浮肿了,已经快要接近死亡了。大夫开了药方,并叮嘱青青,不能让病人吃咸的,不吃盐才利于她治病。肾病就是要保养,想要痊愈,根本不可能。
天已经晌午了,青青挽留大夫吃饭。鱼挑子到海边靠帮的船上买了一条新鲜鱼,让青青给炖上。青青还炒了鸡蛋,擀了面条。平时,家里吃的虾酱臭鱼酱也端到桌子上。
大夫吃得满头大汗,他用筷子指着那些酱说,记住了,患肾病的人,千万不能吃这类酱。因为口味太重,不利于治病。想要多活几年,最好不吃盐。
从那以后,青青就把虾酱臭鱼酱从桌子上撤了下去,不让婆婆吃到这些酱。她做饭也尽量少放盐,有时候也不放盐。服过药的婆婆脸庞明显有了血色,看来,鱼挑子请的这个大夫,开的药方管用,真的是个好大夫。
算计日子,今天,鱼挑子要来取鱼网。一大早,青青扫了院子,并在院门口撒了一层细沙子。因为鱼挑子上门让她织网,这几年,她们一家的日子过得还说得过去,至少手头上能拿得出闲钱。再者,鱼挑子还请来了县城的大夫给婆婆治病,青青想给他做双鞋。他一年到头翻山越岭走路,最费的就是鞋子。没别的报答他的方式,就给他做双鞋吧。
(刘全华摄影)
鱼挑子没有结婚成家,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,并不等于他不想找个女人过日子。鱼挑子不会别的手艺,打年轻时起,他就靠出力气挣钱。手里的那根扁担,就是他挣钱的家伙。那扁担是刺槐木的,要论扁担,八年生的刺槐树做扁担最合适,年头不够,没有老辣的韧性。超过八年,那树木全是筋,几乎没有弹性。选那溜直的槐树干,去掉槐树皮,就取树皮与树心那段材料,细细打磨,不能伤害槐木的每一条经络。打磨到最后,鱼挑子也不用工具,他就用手当作磨具,一直将扁担打磨到扁扁的,两头微微上翘,压着肩膀的地方最厚,厚也厚不过一寸半。这样的扁担上肩,挑上百十斤的重物最合适。挑扁担一上肩膀,挑扁担的人的腰会一耸,迈出极富弹性的一步。随着富有弹性的这一步,那扁担会情不自禁地发出吱嘎一声响。随着响声,那扁担也向上弹起,弹起的那一刻,扁担已经跳离了人的肩膀,挑扁担的人会随着韵律,再迈出第二步。鱼挑子这一路并不是在走路,而是跳舞。扁担为他打着节拍,他就严格地按照这个韵律,腰部到肩膀直直地挺立,而他的两条大腿、两条胳膊都在挥舞扭动,扁担在他的肩膀上极有弹性地跳动。因为他的脚掌也要随着节奏扭动,他脚上的鞋子磨损得最快。每一双鞋子,他都要在鞋底打上一块胶皮。等到胶皮磨损得薄薄的,这双鞋的鞋帮也破得不能穿了。
鱼挑子不会想到,他向往的这个女人会量他的脚板,打算给他缝制一双鞋。他无意踩在细沙上面的脚印,留给了青青尺寸。鱼挑子无意接触青青时,因为总是有旋风网让青青织,一盘盘丝线把他和她联在了一起,鱼挑子总是有借口走进青青家的小院。
鱼挑子织鱼网的这个方式。他和青青开始了交往,他和青青,和这一家人也熟悉了。他知道,他对这个寡妇动了心思。但是,他不能莽撞,他把自己的这个念头深深地藏在心底。青青把他当成了一个给她送活干的人,而他就老老实实地当这个中间人。
这次请大夫给青青婆婆看病,更是感动了这一家人。青青才萌生了给鱼挑子做双鞋子的想法。多次接触,她和鱼挑子除了谈论如何织鱼网,别的什么也没有说过。她对鱼挑子一无所知,几次话到嘴边,又给咽了回去。她要用最结实的布,用织网剩下的线,纳底做帮,给鱼挑子做双鞋子吧,以表达她对他的感激之情。
鞋子快要做好的时候,红英来青青家看望,看到炕头上那双快要做好的鞋子,红英多了一句嘴,想不到,青青嫂子的手艺这么好,这双鞋子是给谁做的?
青青一时给噎住了,她竟然没说上话来。
红英自问自答,是给大海做的吧……
青青随即嗯了一声。
红英啧啧感叹,怪可怜的人哪,好在有嫂子疼他,他这辈子也算没白活。
青青婆也没插嘴,她想留下红英在家吃饭。
红英也不留下,她说,是二大爷打发她来家瞧瞧,看看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。
青青说,没有什么事情,谢谢生产队对她们家的关心。
鞋子做好了,青青想,等到鱼挑子来的时候,她就把鞋子塞给他,让他穿上她亲手为他的鞋子。可是,等到鱼挑子上门时,青青却迟疑了,没有把鞋子给他。那一瞬间,她的脑海里面也画了一个浑儿,成年累月锁在石屋子里的小叔子也没有穿过一双新鞋,也不知是怎么想的,青青把鞋子穿到了“彪”小叔子的脚上。
“彪”小叔子的眼圈发红,眼泪在他的眼眶里面打转。
青青心里那滋味,说不出来,只觉得堵。都说彪子傻子活得简单,说他们四五六不懂。从小叔子的眼睛里面,她似乎也看到了里面的渴望,他也需要量温情,需要关怀。
看到这一幕,婆婆也落泪了。她知道,青青是给谁做的鞋子,青青能把鞋子穿到自己“彪”儿子的脚上,婆婆也感到很欣慰,她可以相信,至少自己去世以后,青青不会抛下“彪”小叔子不管。
婆婆服用县城大夫开的药方以后,病情有了好转。可麻烦的是,药服用完了,必须要到县城里的药铺抓药。抓药麻烦,抓药也要花钱。红英再到家里来的时候,婆婆求她帮忙,给找个偏方,偏方治大病,说不定也能治好肾病。
红英认真对待这件事,她在大会小会上讲,帮助青青的婆婆找个治肾病的偏方。青青的感人事迹已经很多了,可红英还是讲她亲眼目睹青青怎样给“彪”小叔子做新鞋,那个“彪”小叔子给感动的潸然泪下。这说明什么,说明“彪子”“傻子”也通人情也知道感恩。
李大鼻子给找了个偏方,偏方也不复杂,就是用老头草熬水喝,治疗肾病很有效。海青岛的人托亲戚、找朋友,想着法子帮着青青婆婆找老头草。用老头草熬水,一天喝两碗。这偏方虽然不能根治肾病,至少可以维持病情不再加重。
青青婆婆靠着老头草,又维持了两年。在大清爹去世的第三个年头,青青的婆婆也终于病倒了。她的脑袋肿胀得像个笸箩,上眼皮和下眼皮已经挤到了一块儿。其实,婆婆可以多活一些时日,她自己不想再活下去了。青青嫁到他们家,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。婆婆一直不相信,儿媳妇会为儿子守寡。青青的表现,婆婆这辈子亲眼目睹了贞洁烈女,在此之前,她也一直怀疑,儿媳妇能在她们家待多久。直到如今,婆婆相信了,青青会永远在守在她们这个家,这个家里老的老,病的病,婆婆突然感觉到,自己就是个追命的鬼,在消耗着青青的青春青青的命。在婆婆生命最后这半年时光,婆婆偷偷地倒掉了老头草熬的水,她偷偷地吃缸里齁咸的虾酱臭鱼酱。她听大夫说过,患肾病的,第一要禁忌的,就是咸盐重口味。她偷偷吃咸,等于服用毒药,她就是想早点死,早点让青青解脱。她也想,在自己死之前,也给“彪”儿子下点毒药,她要带走“彪”儿子。可是,婆婆死到临头时才知道,人哪,死到临头之际,连下毒药的气力也没有了。
临咽气之前,婆婆拉着青青的手,浑浊的老泪流了下来。她说,青青啊,不知不觉,你也过了中年。是俺们一家人,拖累了你,你跟着俺们一家人遭了罪,受了累。给俺下葬以后,你就改嫁走道吧。
青青只是哭泣,她真的悲痛欲绝。
婆婆又对红英说,你是妇女干部,你要帮青青一把。把我埋了以后,你们把俺那彪儿子送进养老院,把他锁在那儿,让他能活就活,不能活,俺就带他走。真的不能再拖累青青了。
红英说,婶子,俺们不能看着青青不管,青青也不会扔下你老儿子不管。你就放心地走吧,别再有一丝一缕的牵挂。
婆婆走了,她依然牵挂着彪儿子。红英联系过公社养老院,想把青青的“彪”小叔子送进公社养老院。养老院不能接收精神病人,何况他还有暴力倾向,一旦发生伤害事件,谁也负不了责任。这样的人,应当送到县城的精神病院,可送他到精神病院,需要一笔钱。
青青没有这笔钱,她也从未想过送小叔子进病院。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,她可不能公公婆婆不在人世了,她就抛下小叔子不管了。留下他吧,他可能伤害所有人,但他不会伤害他的嫂子。确实如此,只要青青走进那间石头屋子,只要“彪”小叔子看见了青青,他就像一只温顺的小绵羊。这个精神分裂的人在青青的眼里,他就是个孩子。有好几次,青青都想打开锁在他身上的铁链子。邻居们劝阻青青,如果不是他彪得像头恶兽,你公公婆婆也不会狠心将他锁起来。
隔天,红英给青青送来了一只蝈蝈笼,里面装着一只青绿色的蝈蝈。红英是个有心人,青青婆婆活着的时候,她一天到晚能跟青青唠叨。婆婆走了,连个唠叨的人也没有了,小院子里静得吓人。有了蝈蝈,就有了悦耳而清脆的叫声。听了蝈蝈叫,就会有好心情。
起初,青青没有把一只蝈蝈当回事,自从枣树下面挂了这只蝈蝈笼,小院子里面有了蝈蝈的清脆叫声,青青的心情也一天天地舒缓而开朗起来。只要有空闲,青青就会走到笼子跟前,瞧瞧里面的蝈蝈。她发现,蝈蝈这只小生灵很爱干净。它经常会梳理自己的翅膀,也梳理头顶上的触角。蝈蝈的触角又细又长,它用两只灵巧的前足拢过触角,然后用嘴分泌出的液体轻轻的清洗。那一举一动,让青青想起了小时候梳辫子的情景。不知不觉,她爱上了蝈蝈。听蝈蝈叫,看蝈蝈自我清洗,青青的心痒痒的。隔上三五日,青青会把一块浸着清水的毛巾放进笼子,让蝈蝈洗澡。
秋风凉了,蝈蝈死了,小院子里面再也没有了蝈蝈的唱歌声,青青伤心地哭了一回。
青青永远也不会相信,她走进石头屋子给小叔子送饭时,他朝着她伸出了一只拳头,等到他张开拳头时,手心里竟然握着一只蛐蛐。蛐蛐抖动着翅膀,欢快地叫了起来。
青青的眼角湿了,她接过了蛐蛐,没有把它关进笼子,而是放走了蛐蛐。她知道,秋天的蛐蛐也活不了几天,她不想看到小小的生灵死在她眼前。
鱼挑子很多日子没有在海青岛露面了,这一回,鱼挑子出现在海青岛,他似乎苍老了许多,也消瘦了不少。这一回,鱼挑子照旧给青青带鱼线来,好多年了,他始终没有空着手走进青青家的小院。十天半月后,他再把青青织好的鱼网带走。好多年,因为鱼挑子送来的鱼线,青青挣到的手工钱,这一家人的日子好歹过得下去。
青青问鱼挑子,这些天,你是不是生病了?
鱼挑子说,俺以为,俺这辈子注定不会生病。可没想到,一个伤风感冒小病,把俺给撂倒了,在炕上躺了这么多天。
青青说,当鱼挑子出大力,好生调养调养吧。
鱼挑子说,挑担子的脚步可不能停下,一旦停下,可就再也挑不动也走不动了。
青青望着鱼挑子的背景,她看他,背也驼了,腰也塌了,脚步也有了老态。脚上穿的胶皮靰鞡就是废旧的大车轮胎缝制而成。她下决心,这一回,一定要给鱼挑子做双鞋,让他穿着合脚,让他走路舒适。更要紧的,是她想向他表表心意。青青知道,他心里惦记着她。说不好因为什么,她也一直害怕鱼挑子跟她说出他的心事来。这些年,鱼挑子愣是没说出来,这让青青很感激他。
没有织鱼网的日子,青青就坐在枣树下面给鱼挑子做鞋子。纳鞋底子时,细细的麻绳穿过时发出的嘶嘶啦啦声响,像是有人给青青说悄悄话。青青没听过悄悄话,她的悄悄话都是说给自己听的。这个鱼挑子,一定是个死心眼,因为他一辈子就会做一件事情,那就是挑担子,走山路。肩膀上的那根扁担也陪着他度过了青年、中年。本来金黄色的槐木扁担,已经让鱼挑子的汗水、血水给染成了紫红色,闪着光亮。鱼挑子保持着一个习惯,不管走到什么地方,第一件事情,一定要把他的扁担倚着墙角立着放好,他也从来不许别人碰他的扁担,他管他的扁担叫伙计,意思虽给他出力干活的伙伴。走进青青家的小院,鱼挑子总是把扁担放在她家的院门后面。他总是在院子里跟她说话,从来也没有走进过她的屋子。这些天,青青脑子里出现的那些往事,都是这个与他接触最多的男人,映现的也都是他留给她的美好记忆。不用多长时间,青青织好的鱼网,给鱼挑子的鞋子也做好了。算着日子,鱼挑子应该出现了。应该出现的日子,他却没有出现。
(刘全华摄影)
这天晚上,青青辗转反侧,难以入眠。她手里依旧握着那把梭子,梭子尖已经光秃秃的溜溜滑,用力扎她的皮肉,也会会产生痛感。梭子掠过青青的乳房,她没有一丝的激动,欲望已经溜走了,梭子划过的仿佛是块老树皮,她似乎麻木了一般。这些年,手里的这把梭子陪着她入眠,陪着她度过漫漫长夜。就是这把梭子,拖着一根永远也不完的细细长线,为她织了一张又一张的旋风网。圆圆的旋风网,能团团地将海水里游动的鱼给罩住,细细的网眼,连条小鱼崽子也逃脱不出去。青青永远他不会忘记,有一次,她看到船舱里装满的鱼儿。鱼儿们都瞪着圆圆的大眼睛,直直地不肯闭上。她问船老大,鱼儿为什么不闭眼睛?船老大说,鱼儿不闭眼睛,它是记恨打鱼的人。后来,青青婆婆告诉她,鱼儿生下来就不会睡觉,鱼儿一生也不会闭眼睛,不是记恨吃它的人,因为鱼儿生来就是给人吃的。
一连几日阴霾,云雾散去,阳光明媚。在一个阳气升腾的日子,鱼挑子终于又出现在了海青岛。他走进青青家的小院,他来取青青织好的旋风网,他也把手工钱付给青青。鱼挑子要走的时候,青青叫住了他,把为他做的那双鞋子递到了鱼挑子的手上。
鱼挑子真的很感动,这辈子,头一回有女人给他做鞋子,而且这个女人正是他心仪的女人。他百感交集,想说声谢谢,却没能说出来。倒是青青说,谢谢你,这些年,让俺织鱼网,让俺们一家人能吃上油盐酱醋,有病还能吃上药……
鱼挑子把鞋子紧紧地抱在怀里,他幻想着,他把青青抱在了怀里……
青青说,把脚上一鞋子换下来吧……
可他哪里舍得穿上这双鞋,他紧紧地抱着鞋子,生怕有人抢走了他的新鞋子。
青青说,穿上吧,别舍不得,以后,俺还会给你做。你不穿,俺就不会给你做了。
鱼挑子这才脱下脚上破胶皮鞋,换上了这双崭新的鞋子。这双鞋子做得真合脚,鱼挑子一辈子也没穿过这么合脚舒适的鞋。人人小时候都穿过娘做的鞋子,鱼挑子没有过这样的经历。他不知道生他的娘是谁,他只知道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。鞋子穿在脚上,暖在他鱼挑子的心里。他的腿脚似乎轻快了许多,腰板也挺直了。
走出院门时,鱼挑子回过身来说,等下回来,俺再给你带鱼线来。
青青说,等下回,俺再给你做双新鞋。
鱼挑子哼着小调,来到了船靠帮的海头。
出海打鱼的人说,瞧啊,鱼挑子今天唱着喜歌,他是冲撞了喜神了。
海头上的人问,老伙计,今天你要挑多少斤鱼?
鱼挑子说,跟往常一样。
你还能挑得动百十斤吗?
俺说了,像往常一样,装一百五十斤的担子。
筐子里装满了刚打上来的鱼,鱼挑子把一块浸透海水的布盖到筐子的鱼上面。然后,他背一躬,腰一耸,担子就上了肩膀。扁担两头弹跳了一下,他顺势迈出了脚步。在众人注目之下,鱼挑子像是跳舞一样,借着扁担的弹性,向上弹起的那一瞬间,他步伐交替的那一刻。步子越大,他负重的力量越小。他的腰杆挺得溜直,他的脚步像是踩着鼓点,极有节奏感。那根槐木扁担就像鸟儿的翅膀一样,上下颤悠扇合,一开一合地跳动着。他像是掠过海面的海燕一样轻盈,挑着沉重的担子就上路了。
身后的人们大声喊,嗬,鱼挑子返老还童了。
孩子们拍着巴掌唱歌谣:
老光棍,老光棍,
裆里夹着一根棍。
脑子里面一根筋,
专门去扒寡妇门,
日后睡个鳏夫坟。
鱼挑子喜滋滋地骂道,小兔崽子,回家问问你们娘,你们是不是光棍打的种。
鱼挑子的骨子里面有股热流,他似乎回到了年轻时,那时候,只要上路起步,他从老辈子挑鱼的人那里得来的经验,一定要走到身子发热,冒出汗水,这样筋骨才能松弛,血水才能融通,即使到了精疲力竭时,稍稍歇息一会儿,身上的体力又会恢复。鱼挑子已经感觉到骨子里面的那股热流,只要他不松弛,再快走几十步,咬着牙别松劲,一会儿汗水就会冒出来。可力气快要用完了,他的脚步快要失去了节奏,那股热流还憋在心窝里面。不能松劲,不能停下,只要停下来,扁担再上肩,那副担子就像有千斤重。不能停下,再坚持一会儿……鱼挑子抬头望了一眼升到半空里的太阳,透过薄薄的云雾,撒到山野的阳光很妩媚,像是刚刚从被窝里爬起来的姑娘。野草尖尖上面的露珠消逝了,绿绿草尖上面撒着一层金色的光亮。鱼挑子最喜欢踩着小草挑担子,小草给他的大脚板踩下去,又会弹上来,为他助力,给他加劲。扁担吱吱嘎嘎不停地叫,那叫声有些嘶哑,像是从老人的喉咙里面发出的,歇息吧,歇息吧……不能停下,热汗没冒出来,血水没串通开,筋骨也无弹性。扁担的叫声越来越难听,声音越来越嘶哑,嘎崩一声,那根陪着鱼挑子好多年的槐木扁担断裂了,鱼挑子也一头栽倒在草地上。他的身上沁出了一层冷泠的汗水,也撒满了一层阳光……
海青岛的李大鼻子出面,料理了鱼挑子的后事,在鱼挑子独居的那间陋室里面,堆放着好多盘旋风网。这些网,都是青青一梭子一线织出来的,这些年,鱼挑子把挣的钱都买了鱼线,让青青给织成了网,这些网他没舍得动,都好好地积攒在他的屋子里。
李大鼻子告诉青青,鱼挑子死了。
青青的心像是给刀子给戳了一下,他是哪天死的?
大鼻子说,穿上你做的新鞋那天。
青青再也没说话。她关上门,把自己也关进屋子,她蒙上被子,呜呜咽咽地哭泣起来。也不知哭了多久,反正蒙头的被子让眼泪给湿透了。
(刘全华摄影)
青青的小院死一样的寂静,没有了嘶啦嘶啦穿梭子扯线的声音,想起了鱼挑子,青青只能把内衣的袖子上面缀了一块黑布,算是暗暗地悼念鱼挑子。这是她这辈子遇到最好的人,不仅是戴孝,更是怀念。她知道,后半生再也不会遇到鱼挑子这样的人。
光阴似箭,日月如梭,二大爷的孙女要出门子了。闺女出嫁,陪嫁要有四铺四盖,乡下的习俗,四床被子,四条褥子。陪着闺女出门子的嫁妆很讲究,铺盖的针线活要由夫妻双全、儿女双全的老女人来做。谁也没想到,二大爷抱着被面和棉花走进了青青家的小院,他要请青青给她孙女做铺盖当嫁妆。
青青想不通,村子里的人也都想不通。
二大爷说,青青嫂子用她几十年的清白,几十年的善良与贤惠,在咱们海青岛上树立起一块讲孝道讲贤良的丰碑。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,青青占全了,海岛上的人都应该以青青这个女性为榜样。
二大爷开了个头,接下来,红英的闺女出嫁,也来找青青做被褥。海青岛只要有儿子娶媳妇,闺女出门子,海岛上的人都找青青做针线活。不图别的,就为青青能给后生们留下针脚,拖着长线,能延续一个好门风。海岛上的人也有一份心意,借着让青青做被褥,还可以给她三块两块手工钱,让她日子过得舒心一点。
过了两年,海青岛辈份最高的二大爷患了不治之症,临终前,他向支部的支委们交待,好好树立青青婶子这个典型,她是新社会新风尚的标杆,可以给下一代青年人做榜样。新社会不兴立贞洁牌坊,但可以刻下一块碑,把青青婶子守孝守节守寡的事迹记录下来,传给下一辈人,看看老一辈人是怎样恪守妇道的。要把咱们海青岛好家风好门风传承下去。
青青活到了文化大革命,轰轰烈烈的运动刚刚兴起时,批斗地主渔霸。海青岛上也没有地主渔霸,就把二流子李大鼻子当成坏分子揪出来批斗。贫下中渔们边打边审问,你这个大鼻子,占了咱们海青岛妇女多少便宜?
李大鼻子虽然老了,可他还是生性不改,他对批斗他的人说,一辈子啦,俺也记不清占了多少个女人,回家问问你们的母亲去吧。
造反派们一直将李大鼻子批斗致死。他死的时候,眼珠子瞪得溜圆,就像隔了潮的鱼眼睛一样,红得冒血。李大鼻子死了,红英也成了批斗的对象,说她老不正经,偷偷摸摸地搞破鞋。
青婶的彪小叔子是在文革结束以后死的。大伙帮助青婶埋葬了叔子,他的坟墓就在爹妈坟墓跟前,这个不幸的人,只有青婶为他哭泣。他太可怜了,整整给一根铁锁莲锁了一辈子。
安葬了小叔子的那天晚上,海面上飘来了雾气,如同一块巨大的盖尸布遮掩着海青岛。青婶在睡梦中合上了那双曾经很美丽的眼睛。不知她是抑郁而死,还是无疾而终。青婶把她不辈子的事情做完了,她也永远地睡了。小院里无声无息,没有人为这个孤零零的寡妇哭泣。
生产队安葬青青时,有人提议,将那把织网的梭子当作陪葬品吧,它陪了青青婶子一辈子。大家也都赞成,把青青使用了一辈子的织网梭子也埋葬了。生产队的人来收拾青青婶子的遗物。青青婶子这辈子过得清贫,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。
红英掫起了炕上的席子,她发现,炕席子下面猛然现身一个肉乎乎的黑色物件,那是什么物件?红英拿起来让大家瞧。
有人认出了,那是一具雄性的海狗生殖器。很多人虽然没见过这物件,可也听说过这物件的故事和传说。那一刻,屋子里的空气凝固了,谁也不说话,心里的感觉是相通的,那个一直矗立在乡亲们心目中的偶像一下子就毁了,半天没有人说话。
人们的眼睛都紧紧地盯着那具极传奇色彩的物件,却没有人看见,青婶的小腹上,点着一颗已经存在了许多年的“宫砂”。“宫砂”就是吃进壁虎肚子里面的朱砂,把“宫砂”点在少女的小腹,验证少女的贞洁。只有保持着贞洁,“宫砂”才不会褪色。
从那以后,再也没有人提起为青婶立碑的事儿。私下里,很多人将青婶当成了笑谈……
徐铎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大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,近四十年创作生涯,共出版长篇小说7部,中短篇小说及各类题材的文学作品数百篇,逾五百余万字。其中长篇小说《大码头》获得华东地区优秀图书一等奖,并被改编为话剧,获得国家艺术基金项目。中篇小说《记忆红薯》获得辽宁文学奖,多部作品获大连市金苹果优秀创作奖。年,当选“大连市文学艺术界十位有人物”。年荣获“全国书香之家”称号,年荣获“辽宁省第五届最佳写书人”称号。同年,被金州老家授予“终身艺术成就奖”。